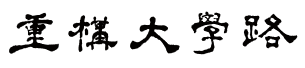重返烏托邦:南國.火燒庄

2020「民雄印象」在地書寫徵文比賽三獎得獎作品
作者/張嘉祥
若是過去庄頭那邊,你會遇到一群野狗,牠們狗多不怕人,尤其不怕囝仔。
在火燒庄的五穀王還看得到橫列成景,被移走前的芒果樹時,那時候的我只有九歲多,剛學會騎腳踏車,一整年裡最期待的是農曆四月二六,五穀王的生日時辰,比過年除夕還高興,那天家裡會來很多人,不認識的叔叔阿姨也好、認識久沒看到的親戚囝仔更好,總會比父母冷戰中讓人窒息的空氣活絡。
那時候的我會被指派一項任務,要去靠近土地公廟的巷子民房中買雞蛋,家裡其實還不放心我,都是姐姐帶著我去。我至今還是搞不懂,那間看去跟平常人家沒有分別的紅磚平房,沒有招牌,沒有叫賣吆喝人客,我姐姐是怎麼知道裡頭有人在這裡賣雞蛋的?
賣雞蛋的老闆是個阿婆,已經忘記她的名字,只記得裡頭燈光不亮,有些昏昏黃黃,一籃一籃的雞蛋就疊在牆旁邊,有些雞屎腥臭,阿婆也不會招呼我們,籃子旁邊有袋子,需要多少自己挑、自己撿,撿完給阿婆秤重、付錢、離開。沒有什麼多餘的話,阿婆也不會想說些什麼,姐姐其實不喜歡來這裡買蛋,在有冷氣的小型超商出現後,賣蛋阿婆就消失在我生活裡。
這群野狗每次都會追著我跑,我對自己的腳踏車跟腳很有信心,從來沒有讓這群野狗咬過,只是牠們吠得很大聲,像我是什麼罪大惡極的人。
小時候的時間過得緩慢,都盼著有什麼會改變發生,尤其想方設法的逃離家裡,逃到空氣軟一些的地方。我流浪在不同的親戚朋友家,有時候會被母親抓回去,我印象中有兩次父親來找我,一次是朋友家,應該是母親拉著他來的,最後被朋友的父親勸回去:
「囝仔留佇這玩嘛無啥物毋好矣。」
另一次父親站在他不願進去的親戚家門口,不肯進來,問我為什麼都不回家,要我回去顧店仔:
「你歸工攏無佇厝,是咧創啥物?!」
我就是趁著他們不注意或者意志薄弱的時刻一次次逃出家門、逃出火燒庄、逃出南國。
在《聊齋誌異》中有記載一則〈野狗〉的篇目。大致上是說在舊時戰場上有一個裝死躲避戰鬥的士兵,在戰役結束後還躲在屍體堆中,忽然所有屍體都站起來說:
「野狗子來,奈何。」
父親是民雄工業區一家造紙工廠的小主管,四月二六這天找了三、四個公司裡的好朋友來家裡吃飯喝酒,平常對於父親的印象就是沉默跟嚴肅,在這一天父親展現出完全不同於跟我們相處時的神情,常常在笑,一點也不可怕或帶有壓迫感。其實在我的記憶裡,我的父親從來沒有大聲怒罵過我,或者死命揍我的行為,他只是沉默嚴肅,在他身上不會找到一點放鬆跟懈怠,連帶著夢和理想都離他遙遠。大學之後讀到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侯孝賢的台灣電影、吳念真的《多桑》我這才驚覺,我的父親就是台灣或者說全世界父親的縮影,是父權社會下《變形記》的「甲蟲」父親。
我的父親在這天暫時「變形」回人,是放鬆和親人的,跟我說了幾個黃色笑話,父親的一個同事來逗弄我,說我是不是不愛回家?我的母親在這個場合是尷尬的,除了傳統父權社會要求母親要帶好小孩的調侃,另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親曾經因為我父親喝酒不回家,就一個人跑去公司聚會現場翻桌,父親同事這句話調侃的可不止我一人,於是母親的聲響可是一點都不小。我記得那年的四月二六父親像敗了興致一樣,草草結束那天的流水席,這次之後,我再也沒看過父親帶他任何一個同事回來家裡吃辦桌。
我遇過很多野狗,有些狗的耳朵或是鼻子很敏銳,明明離得很遠,就看牠從遠方的一個小黑點或小白點,急追至我腳踏車旁已經是龐然大物,狂奔過來要咬碎我。我於是更用力、努力地踩腳踏車,沒有一次讓牠們咬到。
讀書一直不是我擅長的,尤其是學校的課程,那些數字運算和加減更讓我恐懼,高中的時候萬幸考上一間國立的高職,在嘉義來說不算差,只是主要科目是會計和經濟學,經濟學還有趣一些,畢竟還是社會學相關的學科,但是在會計的課堂上我就時常聽到恍神,幾次之後就乾脆在桌子底下讀自己的書,什麼書都看,一開始不會挑書,從小說到歷史、哲學、波特萊爾、甘耀明、吳明益、陳雪、駱以軍各種雜瑣的書。我在課堂上不會吵鬧,老師們也不會強迫一定要專心在黑板上,有種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
這些雜書漸漸讓我有一些自己的心得,輾轉交作品來到台灣的東岸,來到後山唸大學,真的逃出了南國、逃出了火燒庄。在這片後山,在這個專門教授現代文學的科系,我快樂又感覺到自己嚴重的失根和水土不服,不是生理上的,是類似於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異鄉人》描述的那種局外人的感受,我其實沒有特別想念火燒庄,但是總是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它。我的意識裡還是抗拒著回到火燒庄,但是有時候聽著交工樂隊的〈風神125〉就眼眶泛紅,回到火燒庄找以前的親戚朋友吃飯或相聚是沒用的,彼此的生活型態已經不一樣,價值觀甚至語言都已經不再一樣,從童稚到高中青少年階段要好的朋友,從此我們沒辦法再走進彼此的價值核心,在南國,在火燒庄我更直面的體認到,我不止是逃離南國、逃離火燒庄,是逃到連回去的路都找不到,套一句俗濫的文學辭彙,我已經變成「在故鄉的異鄉人」。
那些野狗叫得我害怕又煩躁,這時的我身體還很瘦小,我騎到路邊撿了一根沒什麼懾服力的竹杆,用力往野狗群裡衝去,一邊亂揮舞竹杆。這群野狗突然不復往常的兇惡,四散跑開,留下有些錯愕的我。
這兩、三年回到火燒庄不外乎婚喪喜慶,喜的少喪的多,於是回到火燒庄就像在奔喪。出乎意料的是,自己與父親和母親的關係緩和了不少,也或許是拉開了生活距離之後,從前看來壓迫高大的父親也變得像個普通的中年男子,甚至有些矮小,和我一樣。我也漸漸發覺父親和母親有著自己獨特的方式在照顧我或者關心我,雖然父親反同又父權,母親迷信又缺乏安全感,但是價值觀的不同和家人之間的關心照顧,我發覺可以慢慢慢慢地找到一個平衡點。
我想在我心底還是渴望回到火燒庄的,回到那個時間過得緩慢的村莊,三不五時有騎車過快的大學生摔在斜坡,時不時會有抗議豬舍臭味過重的學生或民宿業者,還有在竹仔跤鏟肥料,停下休息吹涼風的片刻。最好最好能回到時間緩慢的四月二六,火燒庄的戲臺還沒拆,彈珠檯和燒酒螺的攤子會緊鄰,已經成仙做佛祖的阿嬤會牽著我的手去看戲,撿臺上灑落的糖果塞到我嘴裡,村庄外的芒果樹還沒被修剪,遠遠看過去像一條綠色的隧道,我只要穿過隧道就能夠回去,回到高度「異化」之前的自己。
沒有了野狗,我騎著腳踏車從庄頭出庄,往民雄市區的方向騎去,那是另一條更茂盛的芒果樹圈成的綠色隧道,據說已經有百年的歷史。這裡離土地公廟比較近,往左看去就會看見土地公廟,母親和阿嬤嚇唬我說,土地公廟曾經有村裡的阿伯坐在廟裏的凳子上去世,要我少去,我於是更好奇,多跑去土地公廟好幾次,什麼也沒有發現。
穿過隧道後,外面是一條又一條連接彼此到遠方的大馬路,我越往前騎去,火燒庄就離我更遠一些,越來越遠,一直到我看不見為止。
作者簡介
1993年出生,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畢業,嘉義民雄人,火燒庄張炳鴻之孫。一直以來以及目前是臺語獨立樂團「裝咖人」的團長。從事音樂創作、文學創作、報紙經營、藝術行政、舉辦音樂祭、電影編劇、Podcast主持人等,面向貪多不厭的歪桿青年,上個月榮獲文化部紓困2.0全額補助,是目前人生已知最高榮譽的補助項目。
複審老師評語
- 李豐楙: 在抒寫私人生活的感情記憶中,這一篇的主題就是「逃出與回歸」,作者受過科班的文學訓練,在文學技藝與感情表達中,能夠駕馭私密性的親子之情:父母與我,在瑣細的記憶中,借用的意象與動作,諸如野狗、五穀王廟及土地公廟,而這個空間則在真實與象徵交織的「火燒庄」,核心的父母與我,從逃出的衝動到「回到火燒庄」的曲折變化,表現感情的人與物交融為一,在穿過隧道與騎出火燒庄中,最後指向一個再出去而非逃出的現實/真實。就私人/私密感情言,這樣的現代散文有其動人處。
- 楊富閔: 這篇文章以火燒庄為敘事核心,尤其文中的野狗具有高度的象徵意涵。文章涉及故鄉的去與回、失與得、自我與外在的多方拉扯,都在作者真摯情感的鋪成之中,緩慢領引讀者進入那個記憶裡的烏托邦。
- 楊玉君: 緊張的父子關係、逃離、思鄉等常見的文學主題,在本篇的火燒庄中展演,芒果樹綠色隧道成為虛擬的、區隔過去未來的通道,對照近兩年的護樹過程,令人激賞中帶著感慨。個人的感懷聯繫到城鄉的對比,交織出矛盾的情感,具有動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