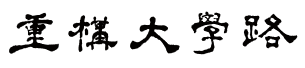杭州旅居記-童年時的回憶

作者/劉兆民 (Chao-Min Liu)
近十多年來隨著世界經濟貿易的急速發展,生活水準的提高以及旅遊業的商業化大眾化,一般人到國外異地旅遊探親居留己成為家常便飯事。我每次出外旅行,來回於安穩舒服的飛機上或遊輪上時總會不自覺地回想起65年前我的母親帶我兩兄弟出國旅行的一段往事。65年前住在臺灣鄉下的人出外旅行是件稀罕大事。尤其是女性帶小孩出國旅行更是不尋常。當時臺灣在日本統治之下,二次世界大戰方熾,我們還能夠離開臺灣到杭州旅行是完全要歸功於母親的毅力與決心。只是母親沒有意料到我們的杭州探親之旅受了戰爭的影響,前後足足地拖了四年才能完成了來回旅程。我的童年也就幾乎都在杭州旅居中渡過。下面的杭州旅居記,也就等於是我童年的回錄。
劉家在民雄
我於1936年8月9日生於臺灣的鄉下地方-民雄。民雄的原名是打貓(註)[1]。劉家從我曾曾祖父開始就已定居此地。滿清末年日本佔据臺灣之前,打猫地區,常被匪徒侵擾。我的祖父劉廷輝(1860-1932)當時年青力壯,又有領導能力,地方人士推舉他出來組織防衛隊保衛家鄉,改善治安,因此在打貓庄很得人望。日本據台後他就任打猫區區長,而後又創辦民雄農業信用組合(現今的民雄農會),擔任第一屆組合長,致力地方经濟的改善振興。他平時又慷慨捐資做公益及廟宇的修建,為地方出錢出力,民雄街仔的人尊稱他”劉總理”。我的祖父可說是臺灣舊農村社会的典型人物。他期望他的兒子們長大後都能和他一樣在地方有所建樹並維持劉家的名望,因此對他的两個兒子管教很嚴格,在他們讀完了書、結婚後,還要他們两家與他一齊住在同一屋簷下。
識新觀念與舊臺灣農村社會的制度習慣格格不入,尤其是祖父的舊傳统想法、因此伯父与我的父親學校畢業後,都有走出鄉下往外發展的意圖。聽母親說‧伯父在國語学校畢業後,就瞞着祖父準備離家到日本留學,祖父得知後很著急,特地跑到基隆,帶他回家不讓他走。當時,一些臺灣富家“阿舍”子弟,藉留学之名到日本花天酒地吃喝玩樂,花了大筆家產後常是學無所成,鄉下人譏笑他們到日本留学是去唸麥仔酒(啤酒)科”。伯父長的一表人才,風流瀟灑,祖父最擔心的是他的大兒子去了日本,也跟其他好玩的有錢人子弟同流合污,所以堅決不准他到日本留学,要他回家完婚。祖父用心良苦,為了留住他、還給他按排了民雄信用組合(農會)經理的職位。伯父有了工作又繼承了一筆財產、也就放棄了他的初衷,在故鄉定居下來。祖父去逝後他接任組合長的職位。
我的父親劉新祿(1906~1984)幼年失母,由外祖母教養。他在基督教学校以及在南師就學時,顯然受了較多的西洋宗教、文化及藝術的薰陶,思想比較開放,對文藝尤其是藝術特別有兴趣。他反對日本的統治,响往孫中山推翻滿清革命成功後的新中國,因此在南師念書時就私下学習北京話,準備到中國上海。當時上海有西歐列强的租界、是中西文化合流之地,到了上海英法租界有如置身西歐,在上海留学可以同時體会中西文化,所以是父親最可行的去處,可是他知道祖父一定不会同意他離開民雄,而且、他是師範學校的公費生,畢業後一定要服三年義務教學才能離職。因此父親在南師畢業後只好回家在民雄公學校教書,一年後(1927)在祖父的按排下和母親結婚。
父親在民雄公學校担任教職時祖父己是67歲。農業社会時代,退休養老,得靠兒子媳婦在旁的照顧,祖父希望两個兒子以及妻室都能和他共同居住在同一屋簷下的心意是可以了解的,只是祖父沒意料到時代已不同、外界對年青人的吸引力相當大、他能留下大兒子已不簡單,要两個兒子都留在家可不容易。父親從臺南回家結婚又願意在家鄉就職令祖父頗為放心。其实父親早己决心要到中國去、回來民雄只是等時间而巳。果然,父親一完成了義務教學之後,就用他三年來蓄存下來的薪水(每月40日元)把妻兒放下、自己跑到上海去學他喜歡的繪畫藝術。父親比伯父運氣好,第一他不是長子,祖父對他比較放任。第二他不向祖父要錢留學,而且祖父那時年紀大了對他也無可奈何。比起伯父,父親意志比較堅決,追求理想的欲望較强,到了十里洋場的上海、有如魚得水、也就流連忘返。當時從法国留學回來的中國藝術家如劉海粟,潘良玉,徐悲鴻,林風眠等第一代中國油画家在上海杭州等地傳授西洋藝術。他們都有很好的中國水墨画的根底之後再到法國研究西画,所以父親對他們的画作頗為欣賞。他到了上海以福建省同安縣人在上海藝術專科學校註冊,專攻油画。他從1929離開臺灣到上海,到二次大戰後1945年間,大半的時间都滯留在中國大陸。
1932年祖父去逝、兄弟两家雖然分了厨房但還是共同住在祖父留下來的大厝,共用大廳和前後庭園。父親因為经常不在家,伯父是劉家的男主人。大伯母因為自己沒有孩子,又很関心男人不常在家的母親,因此常過來幫忙照顧小叔家的子女。母親也很同情伯母被冷落的處境,尤其是祖父過逝後,伯父一家又多了三房四妾,因此伯母与母親妯娌两人相处很好。伯母可以說是生不逢時的超時代女性,因為1890年代出生的臺灣富家女性,大都有纒脚,她就沒有。她不只漢學淵博,對泰西文學也頗有涉獵。她是大家閏秀出身,談吐文雅大方,是個外交人才。伯父對外有了問題都由伯母出面溝通解事。我們雖然住在同一屋簷下,但伯父一家人只有伯母一人和我家大小比較親近。
伯母在民雄街仔是有名的”漢文仙”。光復初,不少民雄的小學老師們不会中文,伯母還開班指導他們學習漢文,一時我家门庭若市,每晚都有老師們來我們家的公廳跟伯母上課。我和小學同學陳嘉珍君也在下課回家後跟伯母學了兩學期的臺語漢文。二次大戰後父親回到家鄉定居,伯母常常過來和父親聊天交談世事。那時代的人,尤其是生活在鄉下的婦女,極少有讀書看報的習慣,伯母是例外。我記得有一天伯母在報紙上看到陳素卿和大陸人戀愛在淡水河自殺的新聞,她很感嘆陳女不該和來歷不明的外省人談戀愛,對着父親說”阿叔仔,你看到新聞嘸?古早人講,一失足成千古恨,少年查某人(女性)可要小心!”,沒想到不到一年後我的堂姊(伯父二房的大女兒)在二二八事变発生後不久也戀上了駐在我家的一個中國軍醫官。伯父為此非常生氣,発誓要把堂姊趕出門。後來堂姊因感染了肺病両年後不到20歲就去世了。可憐的她,伯父給她取的名字剛好就是”惜憐’。
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日軍佔領上海杭州並攻陷南京。汪精衛親日政權成立後,日本佔領軍極需會講中日兩國語言的人員在佔領區做戰地政務工作。父親因為熟悉蘇杭上海地區又兼通中日两國語言,立即被日軍征召,在上海服役。父親在中日戰爭發生之前常來回上海臺灣之间,但被日軍征召之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常回臺灣和家人團聚。1941年秋,我已滿五歲,開始能體會周圍発生的事物,我意識到父親總是不在家、母親告訴我們,他住在遙遠的中國大陸,我們正準備到杭州去看他。可是那年初冬梅山民雄地區發生了大地震,接着是日本偷襲珍珠港對英美宣戰,並以臺灣為基地,進攻南洋英美法荷殖民地。母親計劃的大陸之行也因此一拖再延,到了1942年2月下旬才好不容易啟程。
難於成行的大陸行
我小時侯一直不了解為什麼母親在1941年末的時候決定要去中國大陸。後來她告訴我她早在父親到上海留學的時候就很想跟父親一起到上海杭州觀光,無奈當時经濟上得依靠祖父,當了大家庭的媳婦要奉養公婆不能隨便離[職],因此不敢奢望。公公逝世後,她自巳一個人要養育照顧那麼多的子女,因此她多年來的願望也就越難於實現。我5嵗的時侯母親才32歲,但已是五個孩子的母親。所以當她决定要帶两個男孩到中國大陸探望父親時,劉家的親戚朋友都很驚訝。那時代的臺灣,男外女內很分明,女人絕少自己離家出遠門,何况還要帶两個孩子同行!母親的決定不但沒人讚成(可能伯母是例外),他們還勸告母親要識時務不可輕舉妄動。以當時的時局來考量,母親大陸之行委實不是時侯。當時中日戰爭方熾,雖然上海杭州地區在日軍佔領和汪精衛政權的统轄下平靜無事,整個歐州,北非,蘇聯都已捲入世界大戰的風暴。日本加入軸心国積極準備對英美宣戰,臺灣是日本南進的前哨基地,因此被捲入戰爭只是時間的問題。有鑑於此,伯父認為在那世局非常緊張的時侯,母親不但沒有單身出門的经驗,又要獨自帶两個小孩到戰亂的中國是非常冒險的不智之舉,所以非常反對母親大陸之行。無奈母親是個性很堅强的女性,別人很難左右她的主意。她認為這次不成行以後再也沒機会,因此下了决心非去不可。伯父對她的一意孤行非常生氣。聽大姐說伯父多次勸告不成之後,不得己就和母親妥協,要求母親,如果她堅持要走,至少得留下一個男孩、不要把劉家两個男丁都帶去冒險!當時臺灣社会重男輕女的觀念不只是男人而己、女人也常不自覺地,以男的為優先着想。母親準備只帶我們两兄弟同行的理由是此行只是短期的探親之旅,那時我已是五歲,我的哥哥只大我一歲,都還沒到入学年齡,但己很懂事、隨她旅行不会給她多加負担。小妹還不足三歲,母親委託街上洪家當她的保母。两個大女兒已是小学六年級及四年級在校學生,不能離校缺課,只好留她們在家。伯母很同情母親要去和父親相聚的心意,答應了母親,她会好好地照顧留下在家的女孩,讓母親可以放心去一趟大陸。如果沒有伯母的支持與幫助看顧女孩、母親也末必能夠放心出外。我那時侯知道了我們將要坐船過海到大陸去旅行的消息,非常兴奮。可是两位比我更懂事的姊姊們(11歲及13歲)不能同行、實在太不公平了。她們不但不能同行後來又得忍受四年多無父無母的生活,留在臺灣挨受戰爭期間的苦難日子、誰說天下有公平的事?
母親帶我們到大陸和父親相聚,本來預期最多兩三個月後就要回臺。但天有不測風雲,誰也料想不到我們再回到民雄已經是四年後的事。母親每次談到中國之行時總是非常懊悔。不但去的時侯很不順利,戰後從大陸回臺更不容易。我們滯留在杭州無法回臺時外祖母的去逝更令她傷心不己。
旅途上的撒馬利坦人
1942年二月下旬母親終於準備就緒帶我們兄弟两人啟程。大舅父陪我們到基隆港送別。可是當時資訊沒有今日的快速,母親來到了基隆後,才知道因為日軍大規模攻畧東南亞,臺灣與上海間的客貨輪己不能如期來回两地港口之間,我們上船啟航的日期,也就無從確定。母親從來沒有自己出過门,現在帶两個小孩留落在生疏的基隆,去也不成,回也不是、真是欲哭無淚,不知如何是好。我們住在旅館等船時母親每天都帶我們在細雨綿綿的基隆碼頭望洋興嘆!當時她的着急与挫折的心情是別人難於想像的。
上海碼頭所見
我們離開臺灣時乘坐的船是3千多頓的日本客貨輪。旅客在船上吃睡都在榻榻米的大床上。初春的臺灣北部海上西北風浪還很大,船一出外海母親就開始暈船,塌在床上嘔吐不能進食。我在第一天還碰碰跳跳在船艙內外到處張望,但隔天風浪更大,船乘風破浪在搖擺中掙扎前進,我也開始暈船,倒在床上隨着船身的擺動在榻塌米上滚來滚去。美日開戰後,日本的任何船隻,不管客貨或軍用船,都是美軍潛水艇襲擊的目標,為了安全,船在夜間行駛時實施燈火管制,晚上船艙內一遍黑漆。我們在船上好不容易熬過了三天两夜,在第3天中午前抵達上海。
船到了上海後,停靠在黄浦江岸碼頭。我們站在船上往下看,但見碼頭上人山人海,夾在其中是苦力們以及他們的提貨手拉車与黃包車(人力車),一片混雜。上海的三月天還很冷,他們大多穿着補了再補的破爛棉襖,在喧嚷吆喊声中,爭搶下船客的生意。有些車夫沒等客人是否同意,就先把客人行李拿走再說,客人也只好跟着上車!他們為了生存不擇手段,如果接不到客人也許那天就沒收入可以糊口了!母親巴望在人群中要想找到父親的影子,但眼睛再掙大也看不到他。正在着急時,突然在人海中有一位戴紳士帽厚眼鏡,穿黑色冬外套的人似乎在向我們招手。母親認出他是民雄的同鄉許金田先生後才放下了心。父親不來接我們的原因是,我們的航程一延再延,駐在杭州的父親無從知道我們何時才能到達,因此臨時委托住在上海的同鄉來碼頭接我們。我們坐黄包車離開上海碼頭後隔天就上火車到杭州。据渡航証(出國護照)上的記載,我們於1942年3月8日離開臺灣,3月11日入境中國上海。
在杭州居留
我們一到了杭州才知道此次旅行实在來之不易。1941年底到1942年三個月期间正是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以臺灣為基地對菲律賓,馬來西亞以及印尼加速推進攻戰的時期。因此,基隆到海外的定期船次都受了日本軍事行動的影响,不是停航就是延誤。父親說在這緊張時期中還能夠來到大陸探親觀光是我們的福氣。到了杭州沒幾天,臺滬之间的正規海運果然因戰事的日愈擴大而全部停航。太平洋戰爭開始的最初三個月,日軍南進,勢如破竹。我們剛到杭州時正好日軍攻陷新加波(1942年2月21日)不久,父親對當時的局勢還很樂觀,以為戰爭不會拖久,等到臺滬間的交通復原,我們就可以一起回鄉。誰知日本初期的勝利只是曇花一現。不到一個月在4月18日時,美國的B.25轟炸機在Dolittle將軍的率領下從航空母艦出発,首次空襲東京(有幾架飛機空襲東京之後廹降在杭州西南不遠的衛州),接着是日本海軍在中途島海戰初嚐敗戰,戰局瞬間逆轉,美軍開始反攻,日本轉攻為守,處處挨打,我們回臺的日子也就越來越渺茫。不得己,只有在杭州安頓下來,祈望戰爭早日結束!
杭州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文化古城,南宋建都於此、自古就是文人騷客与藝術家們喜歡逗留之地,馬哥孛羅也到此遊過。市內有他地無可相比的文藝曆史古蹟,加上風光明眉的西湖,四季宜人的氣侯,俗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其來有自。父親在上海留学時就常在杭州寫生作画。1937年底日軍攻陷南京,中國國民黨軍棄守杭州,日軍不戰入城,因此市內沒受戰爭的破壞。我們到達時,杭州是在汪精衛政權管制下,但市內有上萬日軍屯駐。為了我們的到來,父親在他工作地方的對面小巷內租到了一棟二樓公寓,離市中心區及西湖都不遠。地址是杭州市國貨街見仁里七号。以當時的生活水準,我們客居的房子是屬於高級住宅,樓房的上下各有二房一廳,樓上有朝南向的陽臺,厨房和屋身分開,中間有一口水井,有後门通外巷,前庭有高高的圍牆及大門和外街隔離,因此非常清靜,尤其是我們的巷子內有好幾棟同樣的公寓似乎都無人居住。這些房子都是房東所有,戰亂時有錢的人都跑光了,這些房子也就無人租用。我們的房東蕭劍塵老先生是清朝時代舉人,當過浙江省政府教育廳長。他和他的女兒與女傭人同住在很別緻的院子內,我門租了他隔璧的房 子是他的唯一客户。他們一家是我們在杭州4年中唯一有來往的當地住民。
父親在杭州
父親被征召後本來在上海服役,服務單位是日本陸軍中支派遣軍”登”部隊,職稱是軍部屬託。他因專業藝術,被派在日軍文藝宣傳部门工作。日本為了安撫佔領區內當地人反日情緒,與汪精衛政府合作,利用在上海的中國文藝電影戲劇界人士,宣傳中日人民友好関係。父親因工作関係對當時活躍於上海電影界名伶女星如周旋,白光,袁美雲,李麗華等人的活動都很清楚。1941年他因熟悉蘇杭地區,被調到杭州”連絡部”工作,任務是日本佔領軍與當地政府和民間的戰地政務協調,上下班不穿軍服。
父親在1930代就常來杭州寫生作画,他很了解並同情當地人的反日情緒,因為他本人對駐在中国大陸佔領區的日本軍人的傲慢與跋扈也看不過去。然而他不得已在日本佔領軍中服役,內心很是矛盾。据父親說他很幸運在杭州工作時有個很有修養的軍人上司源田東洲。源田少將是日軍杭州連絡部主管,曾留學法國,對文藝頗有修養,尤其精研漢學,對中國經詩字画很有心得,和父親的興趣很吻合。他對唯一臺灣來的下屬特別照顧,因此父親的日本軍人同事也不敢對父親太囂張歧視。父親為了感謝他上司對他的照顧,給源田先生畫了油画肖像。源田少將則以親手用墨筆手錄中國詩抄相贈。父親為了画這幅肖像,把他上司的軍服胸章軍刀都拿回家來做参考。我從小就喜歡繪画,因此對父親作画時的每個步驟,從表張画布,木炭素描到油彩上色,都很好奇地細心觀察。那時給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油彩画的鮮艷絢麗色調。父親作此肖像画的過程,就等於以身示範,給我開始繪画藝術的啟蒙教育,我對油画的興趣從此與時日增。父親自被徵召,在日軍服役以來就少有機會寫生作画,難怪他給源田画肖像時特別興奮認真。這幅肖像画是父親在戰爭中唯一的油画作品。父親在杭州的工作非常穩定,我們也因此才能夠在杭州住了幾年安定的日子。
杭州日本國民學校
1942年4月中旬我們在杭州己有一個半多月,由於臺滬间的非軍用航行船隻己無限期停開,我們回臺灣的日子也從此無法確定,我們两個小孩又都己到了入學年齡,因此父親決定送我們到日本杭州國民學校就學(1941年後所有日本的尋常小學校都改稱為國民學校)。那時侯我的哥哥已七歲,入一年級,我少他一歲,入幼稚園班。為了入學的”口頭試問”父親還特別為我們惡補幾句日語,因為我們在家只講臺灣話,聽講日語都成問題,當時我連自已的名字都不會以日語念出來,要到日本人的學校上課也十分勉強。入學開始、我的級任老師是校長先生的太太,人很和藹可親,是名副其實的”可愛的”老師--河合(Kawai)ヨシコ先生。我的同班約有20幾個孩子,除了我之外都是日僑子弟,男女合班。河合先生大概是因為父親是駐杭州日軍機構的人員又是當過小學老師的,因此對我特別照顧。我小的時候幾乎沒有和外邊的陌生人接觸的機会,尤其是和其他的孩子們,所以一開始就進入連話都聽不懂的日本人學校,和日本人的小孩一起上課,心裡就很胆怯不自在。好在小時候適應力强,不久就和日籍孩子們打成一片。這比我20年後到美國留學,不能和洋人同學交往的困境實有天壤之別。我在杭州日本國民學校三年半是最愉快的學生時代,也是學習效果最好的幾年。我很幸運最初的三年啟蒙教育都在河合ヨシコ先生的班上。現在60年後,我還忘不了她那副親切美麗的蛋臉,班上的孩子們都很喜歡她。她的班上活動都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回憶尤其是唱歌演劇。有一次我還被她選上和幾個同學到杭州日本放送局(廣播電臺)合唱童謠歌曲,現在還記得其中的一首是”鯉のぼり”。父親感激河合校長與夫人對我們臺灣人子弟的関懷,特地邀請他們觀賞”サヨンの鍾”。該部電影是在杭州放映過的日本影片中唯一有関臺灣的電影,1943年由當時在滿州及中國大陸日軍占領區內有名的女明星李香蘭(註:原名 山口淑子,滿州出生長大的日本人,1946年在上海被遣回日本後,繼續在影界活動,後來又當了日本國会眾議員)主演,在臺灣拍製。サヨンの鍾描寫臺灣高山族少女與年青日本警察间的故事,在杭州上映時轟動日本僑界。
我們上學時穿淺綠色童子軍服。我家離西湖邊的學校不遠,經常單獨徒步上下學。後來因為杭州市長被人暗殺,全市實施戒嚴,有一段時間才由高年級生帶隊上下課。我平常下課後就很少外出,和同學也少有來往。只有足田正太郎君因為他家在市中心區經營雜貨店離我家不遠,所以較常去跟他玩。杭州雖然治安良好,對外來的日本人來說還是戰地,為了孩子們的安全,家長都不讓孩子們外出。我除了去過一家日本人经營的文具店白木屋買過文具之外,在杭州四年間從來沒有自己到中国人開設的商店買過東西。我們在杭州的孤立與和本地人的隔閡可想而知。
學童「疏開」
昭和19年(1944)日軍在太平洋作戰節節失利。到了七月初,第一個日本外島領土サィパン島(塞班島)被美軍攻佔,島上日軍與登陸的美国海軍陸戰隊激戰一個多月後全軍覆沒。不久,該島成為美軍轟炸機的基地,日本本土備受極大的威脅。從此我們學校也開始進入戰時狀况。學生每日要帶”防空頭巾”上課。躲防空壕的演習也成了經常的活動。後來杭州也有敵機來襲,市區雖然沒被轟炸,但當天我們躲在防空壕裡真正的體驗到空襲時的滋味。到了那年冬天硫磺島兵失守,接着是麥克亞瑟將軍反攻菲律賓,學校因為距日軍駐地太近,開始實施”學童疏開”以策安全。我們低年班級先移到市內住宅區內的一間洋式大院子內上課。我們的課業一直到終戰為止,都沒有受到日愈迫近的戰火的影響,只是繪画勞作以及課外活動越來越和戰爭有関:寫信給在戰場的戰士,”慰問袋”的裝製,以及募捐献金造飛機的活動佔去了大部份的時間。
1945年春我升入三年級。日軍在太平洋及東南亞的戰線己全部崩潰,美軍在冲繩島登陸。我們每天收聽大本營(日本的戰爭總部)発表的誇張騙人的戰果以及”神風特別攻擊隊”為國犧牲性命的勇敢行為,當時我們天真的小學生還深信,有那麽神勇不怕死的戰士為國家為天皇奮戰,日本一定不会戰敗,尤其是我們住在杭州的日僑,沒有像日本本土的日本人真正嚐到戰爭受苦的滋味,都沒預感到日本的投降即在眼前。
昭和20年八月七日是我們放暑假期中的第一次登校日(返校日),我帶着要交卷的暑期宿題(作業)回校。學生們一到學校和好久不見的同學們再一起,顯得格外歡喜親切。我們先在操場做完了例行的朝禮升旗,接着是校長訓話。但是他一開始就以很沈重的口氣告訴全體師生,日本廣島於昨天(八月六日早晨八點一刻)被美國的一顆”新型爆彈”(當時不知是原子炸彈)炸成廢墟,傷亡非常惨重的消息。當時小學生們還不懂大事,對校長的話並沒什麼反應,但從老師們的表情臉色我們知道事態的嚴重。最後校長率全體師生朝向廣島方向默禱三分鐘致哀。我沒想到這天就是我在杭州受日本教育的最後一天。
八月十五日,一個日本兵軍曹跑到我家來,神情非常激動不安,和父親談了一会兒就匆匆離開了。父親告訴我暑期完了後再也不必回校了。因為日皇在他的”玉音放送”宣布日本向所有敵對國家無條件投降。我聽了暑假後不能再上學時,有點茫然若失。年少無知的我還不知道新時代的來臨,我們的處境尤其特殊,一日之差,從日本國民变成了中國國民。當時,日軍在中國大陸戰場還控制主動,絲毫沒有敗退的跡象,在此時候日本天皇要他們放下武器向經常被他們打敗的中國軍投降,實在是青天霹靂的當頭一棒。在中國佔領區一向威風凜凜的日本人,一夜間成為戰敗國的人,難怪那位軍曹那麽憤怒沮喪洩氣!這位軍曹是我看到的最後一個有武裝(帶 短軍刀)的日本軍人。
母親在杭州
我們剛到的時侯並沒有做長居之計。所以父親常帶我們一家到市內各地名勝觀光,尤其是西湖周邊的古蹟。戰時杭州沒有觀光客,西湖好像特別為我們臺灣來的貴賓開放。春天的西湖翠堤春曉,非常幽美清靜。湖水由蘇堤與白堤分成三部分。湖中有三潭印月加上堤上的柳樹,風光明媚令人流連忘返,難怪古時候蘇東坡白居易两大詩人在杭州西湖得了那麽多靈感寫了不少名詩。父親也在西湖各景點画了不少寫生。我們在湖上扁舟,在湖辺的岳飛墓,博物館,古寺廟遊歷。65年前在戰爭期間我們有這麽高級的旅遊享受,实在難以想像。母親當然非常高興不虛此行。可是我們僑居杭州近4年中最委屈的還是母親。
母親在人地生疏的中國客居一久,回臺灣的日子又無定時的時侯,開始懷念故鄉,故鄉的女兒以及親人們,尤其是當外祖母突然去逝她不能回臺奔喪更使她傷心不已。反之,僑居在杭州對父親和我們小孩子來說,並沒有特別有異鄉人的感受。杭州無寧是父親最喜歡居留的地方。他熟悉當地的社会環境地理,欣賞當地的風光古蹟藝術文化以及江浙地區的名菜美食,難怪他來了中國大陸之後就不想回台長居了。我們小孩子,除了剛入日本人學校時有點生疏膽怯之外,也很容易適應在杭州的學生生活環境。只有母親最嚐受到異鄉人孤立的滋味。她不懂當地語言,不識市街巷路,和外界的人接觸範圍止於住宅近傍的小菜市場。父親的日本軍人同事幾乎都沒家眷在旁。因此她也沒有和在地的日本婦女們交往的機會。當地人當然把我們當日本人看待,多少有敵對心理,不願也不敢与我們來往。那時杭州另有一家臺灣人,是雲林古坑的陳熊中醫師和他的药劑師太太,在市中區開西药房。我們剛到杭州時還和他們一起到西湖玩過,但以後两家並沒有多大來往。也許他們每日忙於診所药房的生意,沒有時間和新來同鄉的我們打交道。1943年夏天三弟出生,母親更沒時間外出與外界接觸。後來有一位父親的同事女川先生剛結婚,暫時借用我家樓下房間居住。母親終於有個婦女伴在家一起聊天的機会。可惜他們新夫妻一開始就相处不來,太太常被先生毆打,我家被他們经常吵架弄的鷄犬不寧,他們住了不久後,父親因不喜歡這位女川老兄的德性,就請他們走路。母親在杭州孤立的生活到了1944年冬才有些改变。我們班級疏開到市區後,為了在冬天寒冷的時侯小學童們在中午有熱餐禦寒,每個學生的母親都得輪流到学校煮熱湯給全班学生吃中餐。在那時侯母親至少有了和其他家長太太們接觸的機会。疏開地的教室冬天沒有暖氣設備,我們每天中午,有熱みそ汁(味噌湯)下冷便當的飯,真是一大享受。
父親在杭州服軍役時薪水薇薄,只靠他的薪水實在不夠維持一家4口的生活。幸好劉家人口多,他可以領取全家8人(包括在台灣的姊妹)份的糧食配給,因此足夠應付我們在杭州的家計,也讓他的同事們羨慕不已。戰時糧食非常缺乏尤其是白米的供應,所以價格特別高昂。母親常以吃不完的米糧支付房租或是在菜市場換取副食。比起日本本土或台灣,僑居在中國佔領區的日本人,尤其是住在蘇杭產米地區的我們,可以說是得天獨厚,住吃都很少受到戰爭的影響。
1945年二月初美軍在硫磺島登陸,经過一個多月的苦戰終於在3月25日把日本守軍消滅。眼看太平洋戰爭的局勢每况愈下,杭州的日軍當局也不得不準備把在地的日僑徹回日本本土。不安的氣氛開始籠罩日本僑界,我們的校長的家屬,我的級任老師在內,是第一梯次撤回日本的僑眷。我們是軍屬也是被勸告疏散回國。有一天父親拿回來一大袋足夠一個多月旅程用的乾麵包鯨魚罐頭等食物,準備必要時也得把我們移開杭州以策安全。我們從臺灣來的”日僑”,在此時侯,因為海路早己不能通行,實無法疏開回到臺灣的可能。因此,如果必要離開杭州的話也只有跟其他日本人一樣從杭州北上,经過北京,滿州,朝鮮的陸路回日本”內地”。母親認為路途這麽遠又費時日的旅程,要她一個人帶着3個小孩(再加上她己懷胎4妹)上路跋涉逃難,她絕對不幹。幸虧,母親的堅持不動,我們沒有上路。因為我們聽到撤退的日僑列車往華北滿州路上,時常被中國國共两方的遊擊隊襲擊搶劫,在旅途備受折磨,更有不少傷亡。在戰時,人的命運就是那麽難預測,逃難的人遭殃,沒上路的人反而安全。我們決定留在杭州的人只有聽天由命等待戰爭的結束。1945年八月十 五日日本投降之日是母親特別高興的日子,因為她期望了3年半的回鄉之日終於有 了希望。可是上蒼有意再折磨她一些時侯,當在華的日僑一個一個地被遣送回日本 土的時候,我們還得再等8個月後才得上船回台。
歡迎國軍來杭州接收
昭和天皇下召日軍放棄武器接受無條件投降後,杭州的日本人好像在一日间全部銷声匿跡。8月15日後父親再也不按時上班了。後來聽母親說,當時父親工作的杭州日軍連絡部正準備放棄一切,在9月初中國軍隊未入城接收日軍遺留財產物資之前,要讓父親据有所有部內的物資,因為只有他是臺灣人,身份在一夜間由日本籍变成中國籍,不會成為中國軍的俘虜。當時父親如果想發戰後光復財,在此時侯大可乘機大撈一筆。可惜他沒有賺錢命,一介書生個性憨直,他認為這些日產本來就是日軍從當地人征收來的物資財產應歸還他們,那能据為己有?因此部內的資產原物不動只等重慶的中國軍來接收。父親告訴我們,時代己不同了,何時才能回臺灣也無着落,因此要我們開始學中國話。他用王雲五註音符號ㄅㄆㄇ開始教我們中國語拼音,帶我們到當地人的小學参觀,並建議我們去上中國人的小學。我第一次到中國人的小學門口,看到了學生中竟有穿開擋褲光着屁股上学的(可能是幼稚園班)!我心裡想世界上那有光屁股上學的學校?因此死也不願意去上中國人的學校。現在回想起來我應該聽父親的話,我來中國4年而沒學到一句中國話也太不像話了。
到了八月底或是九月初的一天突然有一大群美國空軍P..51野馬式戰鬥機群飛到杭州上空,我們開始意識到新時代的來臨。我看到這些紅色機頭,藍色軍徽,銀白色發亮的飛機,以難於想像的速度低空飛過我家陽臺上空,委實壯觀。那時中國軍隊還沒入城,杭州仍在日軍手中。美機先來示威大概是有意要警告日軍不可輕舉妄動!隔了幾天的一個下午,我突然聽到有人在敲我家的前门。我們平常都由後門出入,前门幾乎沒有打開過,所以好奇地把门開了一小縫看看到底是什麽人,我抬頭一看嚇了一跳,原來站在前面的人是一個中國士兵。父親早已告訴我們重慶的中國軍隊即將來杭州,却想不到已來到我家門口!這位士兵,穿草黄色粗布軍服,脚上穿着草靴,手上帶一把掃把。他看我是個小孩,一聲不響就用力打把大門推開,直入門內在樓下四處張望後就開始打掃樓下的空房間。我被他的穿着及舉動嚇呆了。後來才知道我們的住宅己被中國軍方佔用!小兵來打掃房間是準備給重慶來杭州接收的安少將以及他的家眷居住之用。隔了一両天,我們看到士兵用篇担挑了不少行李棉被以及飯鍋臉盆等家具進駐。我們一家人眼看着這些,連杭州在地的人(蕭舉人)都看不慣的,戰勝軍人及眷屬們在我家出出入入,實在非常驚恐不安。尤其是,我們在一夕之間從日本籍变成中國籍,父親又在中國人恨透的日本軍中工作,因此有被當漢奸處置的可能。那些日子是我們全家在杭州生活期間最沒有安全感的一 段。
來此不易回鄉更難
那年十一月我們終於結束杭州的生活,開始等了己近4年的回鄉之旅。我們以火車先搬到上海,父親立即乘軍艦隨軍回臺。他委託住在上海的同鄉朋友郭先生照料我們大小,暫時留在上海等侯回臺的船位。母親帶我們四個小孩(四妹剛滿月不久)寄宿在郭先生在上海北四川路附近小巷內租的房子。郭先生是臺灣大林镇人,在上海经商,太太是浙江紹興人,沒有子女但收養了一位十四歲的養女,宝宝。他們一家和我們一樣,也在上海等待回臺的船位。两家八個人擠在只有两间房的屋內。我們是依人籬下的客人,五人擠在吃睡都在同地的小房間。上海的冬天陰濕又寒冷,房內又無暖氣設備,那時我們真正的嚐到在異國流浪困苦的滋味。當時四妹才出生不久,三弟也不足兩歲,母親在那生活條件極差的環境下要照顧4個小孩可真不容易。我們這九歲與十歲兩兄弟不上学也不敢出门。每天的工作是替母親洗尿布。冬天雨多,温度又低,尿布不容易涼乾,小小房間到處吊滿了濕濕的尿布,用取暖的小木炭火爐日夜烘烤也來不及烘乾。那時上海市內雖然己有自來水設備但沒有熱水裝置,每天用冷水洗尿布時兩手都被凍的發紅。雖然如此,我們全家都沒生大病,實在是幸運。
戰後的上海
我們在上海侯船本來以為只是短暫的停留,那知一天過一天回臺灣的日期似乎越來越渺茫。更遭的是,日本投降之後正是國共內戰的再開始。蘇聯幫助中國共產黨掠奪滿州內蒙古地區,美國支持的國民黨從重慶出來接收江南,華東。他們所到之處無不給當地人帶來貪官污吏,腐敗政府。當地人心裡有數,抗戰勝利是大災大難的開始。我們來到上海時街上常看到成群的叫花子(乞丐)向過路人討食討錢。冬天天冷,他們無處熱身,只好搶着抱在煙窗取暖。飢寒交迫而凍死的屍體是路邊常見的光景。當時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貶值,一瀉千里,後來折成金元券銀元券都無法挽回破產的经濟。快速貶值的貨幣很快的把母親手上僅有的旅費耗盡,米飯变成奢侈品,發酶的玉米粉成了主食。我們本來是回鄉的旅客,但是在上海日久,越來越像無家可歸的難民。到了1946年3月初我們在上海已熬過了5個多月的冬天,回臺之期仍無着落,母親不得不要求父親從臺北匯款過來濟急。
** (註:現今的公賣局。日本据臺後在臺灣特別設立菸酒產銷控制的機構[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推行在臺灣的殖民地政策。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後不但沒有毀除專賣局還繼續維持菸酒的專賣制度至今仍然沒有開放民營)
回到台灣
我們乘回臺灣的輪船是一艘近萬噸的老貨船。船身吃水太深只能停泊在黃浦江中不能靠岸接客。離開上海那天,我們大小和郭家一起先以小舢舨離開陸地碼頭,到了貨船身邊再以繩梯上船。上船時我哥哥背了两歲的小弟,我背着小妹從晃動的小船与繩梯爬上約有十幾尺高的甲板上。我們一上了船以為有床位等我們的到來,那知道,這條大船只有一间有如倉庫的大貨艙,而且裡面的每一空间都早己被上百千的旅客以及他們的雜亂行李堆佔据。整個貨艙有如沙丁魚罐頭,被擠的水洩不通。船上旅客絕大多數是去臺灣接收的中國官員家眷或是軍屬,難怪他們優先早我們上船並佔据了艙內的空位。對母親來說我們能夠上船回臺已是謝天謝地,再差勁也得忍受,我們就在甲板上的一卷大繩上安頓下來。幸好四月底的天氣己比較暖和,也沒下雨,露天甲板上的空氣新鮮,睡在艙外實在比在艙內衛生的多。貨船上除了沒睡的地方之外,當然沒有盥洗及沐浴的塲所,也沒有食堂供食,因此所有旅客都得自備糧食飲水。最不方便的是要”方便”的地方,船上只有四處用木板臨時在甲板上搭成的簡陋厠所,船上每天都有上千人要如厠!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的船就像越戰時,越南的難民(boat people)的逃難船。當時沒有照像機,沒能把這歷史性的場景拍照下來做個紀錄實在遺憾。我們離開上海不久,船艙內有一旅客看到母親帶着两個嬰兒又會暈船,好心的讓出了一小角落給了母親有個可以躺下來休息的地方。母親雖然挨受海上旅行之苦,但我很少看她有如此心安愉快的時侯,雖然船上的條件如此差勁,但對我和大哥來說,只要有吃的,隨時隨地都可睡可玩,回臺灣的海上三天两夜就好像最近的郵輪度假之旅。
我們的船開始駛出黃浦江時,江水從黃濁色变成淡黃色,最後出了長江口進入大海時,所見的是一片深藍帶綠的海洋!只有我們的一條船很孤單地默默前進。第二天天氣良好,海浪稍為大了一些,船破浪前進,船頭两側激起的浪花在陽光照射下顯得額外壯觀。第三天早上,我們看到成群的海鷗隨船伴行,告訴我們離開陸地己不遠。不少旅客開始跑到船的前方瞻望,等待綠色臺灣從水平線出現。這時母親更迫不急待,她已開始做下船的準備了。果然過了不多久,突然有人激動地叫喊,臺灣到了!臺灣到了!整個船上的旅客也開始騷動起來。
那天不到中午時分,船慢慢地經過和平島駛進基隆港時我看到整個港口受戰争破壞的後果。基隆港大概是大戰中被美軍轟炸最徹底的一個海港。港內周圍所見到處是爆炸破壞的痕跡,港內堆滿被炸毁或是沉沒的大小船隻,碼頭上也沒有一個完整的建築物。船上的人被周圍的景觀看的啞口発呆。我們的船無法靠岸只好停泊在港中深水处準備給旅客下船。這時我突然聽到有人在一條小船上用臺語叫賣香蕉的聲音。我好久沒聽到鄉音,他的叫賣,聽來格外親切,好像在向我們說WELCOME HOME !
當我們的船進入基隆港時,剛好看到許多在臺日僑帶着有限的行李,很有秩序的在碼頭準備上美軍運輸艦被遣返日本。反過來看我們雖然是戰勝國,來臺接收臺灣的中國官方眷屬,却乘了一條老舊貨輪,如同逃難的難民來到基隆,下船時更是爭先恐後,吵雜無序,不禁令人疑惑到底誰是戰敗國的人民?
母親一下船後第一件事是要去拜訪四年前在基隆時幫助她的恩人,並準備禮物要登門道謝感恩。可是這位好心人的住區已被空襲破壞而面目全非。母親已無法找到我們住過的小巷內的房子。父親還陪了母親在港口附近打聽了好久,但已無人知道這位恩人及他女兒的去向。
我們回到臺灣的第一天就到了臺北。臺北是日据時代日僑最多的城市,日本人被遣返日本後,留下很多官舍及日僑家屋。大陸來臺灣接收的官員,只要用一帋行政長官公署屬下機構的信箋用毛筆寫上某某機関官員住宅,帖在這些空房的门前,就可以永久佔用居住。父親隨軍回臺後即在台北市的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煙酒專賣局做事,因此他也分配到了一棟非常寬敞的日式住宅。我們住慣了簡陋擁擠的上海小公寓,回到臺灣,忽然能夠搬進在臺北給日本官員居住的高等官舍,實在有點受寵若驚!尤其我們小孩都很高興,以為我們就会長期居住在台北。可是母親一心只想回鄉,對在外地的生活已感到非常厭倦,再有多好的房子,她也住不下去。我們在臺北住不到兩星期就舉家搬回民雄。父親也只好申請調職,回到故鄉在嘉義專賣局任職。1946年五月中旬我們終於回到久別多年的民雄故鄉,這是一九三0年以來全家第一次的團聚。
後記
1)自從1945年八月在杭州離開了日本学校後一直到1946年9月,我整整曠學了一年。我去中國學了日語,回到民雄進入民雄國校才開始學北京語,難怪我的两種語言都学不好。
2)父親又回上海。1947年秋?父親辭了專賣局的工作。他的朋友知道他很熟悉上海,就邀他合作,從臺灣運送一批活的火雞到上海市場(趕上聖誕節)再装運脚踏車零件回臺銷售。据母親說,父親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子,他只是借機会想再回上海罷了。不久國共內戰大陸淪陷,父親從此再也沒有去大陸的機会。
3)1947年2月底,二二八事變發生不久,我家被一連隊的中國軍隊佔用了約一年。我真的沒想到我們在杭州的遭遇,不到兩年後會在自己故鄉老家再重演一次。
4)再和母親一起旅行。1970年以後,臺灣经济起飛,臺灣人開始流行出國旅遊,父母親也很想到歐州各國遊覽,但他們己上了年紀、行動遲頓、不敢參加臺灣的旅行團出遊,因跟團大都是行程急促,服務品貭極差,他們怕在旅途路上,如果跟不上人家會被放鴿子。1979年他們來美国居留了幾個月,我便建議和他們一起到歐洲一遊。但之前,我從來沒有去過歐洲大陸,現在冒然要同两個老人到歐洲各國自助遊覧,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好我當時還算年輕,自己又喜歡有冒險性的旅行,因此說去就走。我們出發前並沒有預訂在歐洲的旅館住宿、從紐約起飛經由氷島到盧森堡後,租了一輛小車子,用地圖當响導,三個人就在歐洲大陸遊歷了20幾天,走遍了西歐10個國家。當時我身兼司機和導遊,在從來沒有去過的陌生異國,每日得按排住食、觀光、旅程,託上蒼之福,平安無事完成了整個旅程,我每次回味那次和母親一起的旅行的經過,就會聯想到小時候杭州之行,也加深了我對母親的懷念。
[1] [註: 日本佔領臺灣後,打猫两字,以 日語的字音た..びよう,念起來很近似民 雄(Tamio たみ を)两字的讀音,所以日語化改稱為民雄。 (同樣的現在的高雄 (たかを)可能是來自打狗(た-こう)的日語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