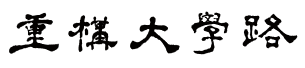劉兆民習畫自述 ◎Chao-Min Liu 劉兆民 | Taiwanese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

劉兆民習畫自述
1.啟蒙時期
我出生於台灣鄉下的民雄,但住在民雄的時間很短,一生注定漂泊,當出外人,不過生活在故鄉的一段時刻,可以說是影響我後來志趣最大的地方。
我住在民雄最長的時間是出生到五歲,也是我的記憶中最空白的一段。現在猶能記得的: 有嘉義地區 1941 年 12 月 17 日的大地震,那次地震把家裡一座假山上的一塊大石頭震落下來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另外記得的是家裡有一窗子很大的房間,家人都叫アトリヱ(Atelier),裡面掛了不少畫,另有書籍及石膏像的東西, 從母親口中知道這是父親工作的地方,但他在遙遠的中國大陸我們正準備去探訪他, 這是 1941 年底的事。
我母親從來沒有獨自出外旅行的經驗,現在要帶孩子到語言不通,風俗習慣不同的戰亂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很膽大冒險的事,伯父母舅父們都替她耽心,外祖母尤其反對, 但母親是一個意志堅決的人,那裡會聽他們的勸告!那時候她有三女二男,雖然預定的旅行是短期的,但路途遙遠,要帶這麼多孩子出遊是不大可能的事,所以決定,妹妹及二個在小學就學的姊姊留在家由伯母照顧, 只有我兄弟兩人和她一起去中國。對我來說,我們要離開鄉下到生疏的異國是很興奮的事,鄰居的小朋友們都非常羨慕。 兩位比我們懂事的姊姊不同行令她們非常失望。那時台灣社會重男輕女,她們不但不和我們一起去杭州大陸,後來又得忍受 4 年半的無父無母的生活,受盡戰爭期間苦難的日子,誰說世間有公平的事。
母親帶我們兩個男孩到大陸探訪父親,本來預期一個月就要回來的。但天有不測風雲,誰也不會料想到我們回到台灣是四年半後的事。母親每談到此行莫不非常悔不當初,尤其是我們留在大陸歸不得的時候,外祖母去逝更令她傷心不已。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同時進攻菲律賓,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台灣成了日本南進的基地。戰爭一開始我們的旅行就有問題。我們先到基隆,卻因戰爭的關係,基隆到上海的客船已不能定期來往,本來預定的時間一延再延。我們為了等船只好留在基隆, 去回不得。一天過一天在港口望洋興嘆, 母親的著急可以想像。如此這般我們竟在基隆“流浪”了一個多月,才上了船。我們的船一起航,怕美國潛水艇的攻擊,船上實施燈火管制 。冬天海浪又大,母親在船上暈吐了三天,好不容易熬到上海黃浦江碼頭。我們到了上海,父親委託住在上海的同鄉許金田先生到黃浦江碼頭接我們,當天乘火車從上海到杭州。
我們靠天公保佑平安到杭州和父親團聚時已是 1942 年 2 月 28 日。父親在年輕時不滿日本對台灣剝削、榨取的殖民政策,在台南師範時就暗中學習北京語,義務教學三年後,就到上海藝術専科學校念書並滯留在江浙地區有十幾年,以在杭州的時間最長。他很同情當地人飽受軍閥內戰及日軍侵佔的苦難,沒料到在中日戰爭之後,自己反而被日軍徵召,在日軍中服役,心裡很是矛盾。當時駐在中國的日本軍人威風凜凜,父親對他們的跋扈傲慢,非常看不過去。據父親說他的上司源田先生是例外。
源田東洲官拜日本陸軍少將,留過法國,對文藝頗有修養,尤其是漢學,愛好字畫,和父親的嗜好興趣相近。大概是這個原因,他似乎特別照顧唯一台灣來的下屬,並委託父親為他作肖像畫,又以親筆寫下中國詩抄相贈。當時台灣人在日本軍中有機會和將級軍官接觸的人大概沒有,因此父親的日籍同事軍人也因而不敢對他太囂張歧視。父母親也幾乎不和他們來往,來家的訪客中倒是中國人比日本人多,我第一次對油畫的世界有些模糊的見識,就是在父親為源田少將畫肖像的時候,父親花了很多時間與工夫完成此畫,作畫時他把源田的軍服、勳章都拿回家來。我從小學下課回來就沒地方去,也很無聊,因此父親在作畫的時候我特別能夠專心去觀察他的一舉一動。從頭到尾在他旁邊注意他如何準備 Canvas(畫布),用木炭筆打稿,再用色料一筆一筆畫上去,鮮艷絢麗的油彩像牙膏一樣被擠出在調色板上,加上 Linseed Oil, Turpentine 的特種嗅味,印象特別深刻。我對油畫有興趣,大概就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在想有一天也要把這些油彩擠出來塗塗看才過癮。
1945 年 8 月 7 日廣島被原子彈毀滅,剛好隔天是我們暑假中的一個“登校日”。校長在早會時宣布廣島被“新型爆彈”炸毀,死亡慘重的消息,率全校師生向廣島方向默禱三分鐘。這一天也是我上日本學校的最後一天。不到幾天父親告訴我再也不必回學校了,原來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無知的我還在準備暑假“宿題”回校時交給老師。
我還記得 1945 年 8 月 15 日那天日皇廣播無條件投降,有一日本軍曹(士官長)來家,很激動的和父親談了一會兒,又匆匆離開,從此以後我再也沒見過一個武裝的日本軍人。
母親自從到杭州以來一直想早日回台灣的故鄉,好不容易苦等了四年,以為戰爭結束了,可以回去了,那裡曉得上蒼卻特別要為難她,回台灣其實比來杭州更加困難。戰後很多滯留在江浙地區台灣同郷也都急著要回台灣卻回不得。
父親先被中國軍方遣返台灣但不准他的家眷同行,不得已, 只好把母親和孩子們留下,隻身先回台。
當時母親的處境就如 4 年前在基隆侯船的情況一樣又得帶小孩留在上海候船回台,可是這次上路不只帶我們兄弟兩個,又要照顧在杭州出生的三弟與四妹。
中國雖然是戰勝國,卻只有兩條貨船當做客船來回上海基隆,主要用來運送到台灣接收的官方人員家眷。因為他們有優先,我們不得不等候。我們就如同逃離家鄉的難民,先是從杭州搬到上海,在上海又等了半年時間,才輪到我們搭上回台灣的海輪,結束我們在中國大陸的生活。回台後親戚朋友們都稱讚母親的能幹!但是他們那裡能夠體會到母親的心情?
1946 年 4 月下旬我們終於上了像擠沙丁魚罐頭的貨輪從上海開到基隆。基隆港口到處被美軍炸沈的船隻炸毀的碼頭, 市區被戰爭破壞的痕跡已不像我記憶中的基隆港。我們的船只能停泊在港中不能直接靠岸。我們在等候下船時 突然我聽到有人在一條小船上用台語叫賣香蕉的聲音,聽來格外親切,好像在向我們說Welcome Home!
我們的船進入港口時,正好有很多在台日僑有秩序的在港口上美軍軍艦被遣回日本。反過來再看雖是戰勝國民乘坐的貨船,裡面卻雜亂無章,擁擁擠擠如同逃難的難民,不禁令人疑惑,到底誰是戰敗國人。
2.住在畫室的時候
1946 年 5 月經過了四年半後。我們終於結束了大陸的“旅行”,回到民雄故居。
我進入民雄國民學校四年級。不到一年 228 事變發生,我家的大廳及庭園被大陸派遣來台的一排 軍隊佔用了好幾個月。接著是通貨膨脹,大陸撤退,白色恐怖,父親的幾位朋友也莫名其妙地被捕入獄。父親忙於生計,已無心也無暇作畫,我家又多了一弟三妹,父親的畫室(アトリヱ)就成了我兩兄弟的臥室。
我家的古厝和伯父母一家共居。父親在古厝後庭另建造一日式 8 疊房子和他的畫室相連。畫室的南邊是一座以天然的大石塊堆砌而成的假山造園。畫室朝北方的大窗是標準的 Atelier。除了畫架,有各種石膏像及石膏製的球體、錘體、正方體及圓筒體等基本美術教材工具。牆壁上掛著父親的一些畫作,他收藏的一些古董、陶器、書籍、唱機、唱片也都存放在內。這間畫室對我來說是一間小 Museum。我住在裡面對這些東西都很感興趣,尤其是美術雜誌畫冊、圖畫比字多,看圖識字印像特別深刻, 無聊的時候就翻閱這些畫冊。因此,我在小學的時候已大略知道一些西洋畫家們的名字及畫風。如畫裸體肥胖的女人的畫家是ルノァル(Renoir),畫靜物水果有名的セサンヌ(Cezanne)。畫奇型怪狀人物的畫家是 Picasso,我小時候就喜歡東搞西摸以及塗鴉,小學時的美術勞作課是我最期待的科目。父親知道我對美術有興趣,就叫我用畫室的石膏像物體為對象,練習物體光暗形狀的圖型表達,用自己的手掌為目標練習 Drawing,或用鏡子畫自己的肖像。因此我在小學六年級時對 Drawing 已有相當的基本訓練。我在五年級的時候學校來了位美術老師。
他看到我的 Drawing 與用水彩 Crayon 上色是經過一些訓練的,而且作畫技能已很有基礎,就問我是跟誰學的,我告訴他我父親是個畫家。有一天晚上他來拜訪父親,在他們的談論中我知道這位美術老師從來沒有用油彩畫過畫。父親建議他用クレパス(Oil pastel)以及鄉下土造的“土紙(衛生紙)來作畫可以得到油畫的效果。那時候台灣的經濟幾乎破產,要用畫布以油彩作畫,經濟上不但不可能也不容易買到這些材料。父親的油畫材料是戰爭以前留下來的,物以稀為貴,也就不給我用油彩練習。我從那時候開始就常以 Oil Pastel 著色,做Sketch drawing 時更覺得方便。
1948 年我因為沒有考上離家較近的嘉義中學,父親建議報考台南長榮中學。原來父親在長榮中學念過一年的書(後來轉學台南師範),所以對長老教會創辦的學校早有認識。我被錄取後準備離家上中學時,心裡有點膽怯,但每次想起小學畢業時唱的離別歌中的一句,…男兒志在四方…,也就硬著頭皮假裝高興,離家寄住學校宿舍。我從大陸回到民雄不到三年,又再次離開故居, 只是這一次是自己離家出門。
長榮中學是英國長老教會在台灣創辦歷史悠久的一所中學。當時有一位英國來的傳教師 Mr. Singleton 教我們英語。除了國文老師之外,全部用台語上課,宗教氣氛很濃。每日朝會有聖經道義的講解,常由校長趙天慈先生主持,另外神學院院長黃彰輝先生及教會總幹事黃武東先生也常來講道或講解聖經故事。我們鄉下外地來的學生,住在校內宿舍,管理嚴格,有如修道院,一天內除了下課後 3 點到 5 點是自由運動時間之外,吃了晚飯後,每天又有半小時到一小時的禮拜,唱詩聽道,以後兩個半小時是自習做功課時間,晚上十點熄燈就寢。
十個學生睡在一個大蚊帳內。早上 6 點由舍監用吹哨叫醒我們,整理房間打掃,吃早膳後上學。星期日早上又得到台南東門教會做禮拜。
當時正是大陸撤退,韓戰開始前後,食物及日常用品都很缺乏,我們寄宿生每兩星期六就得回 鄉下帶一斗米(14 斤)回校才有飯吃。我們幾乎沒吃過零食,只有星期六下午有機會外出,拖著木屐走到 台南 西門町 さかりば 吃一碗鱔魚麵是一大享受。
在那時代思想被控制的教條式教育制度下,一般中學生在校 能學到的只是指定教科書內的知識,課外讀物 可以說幾乎沒有。 在 長榮中學念書的學生 要多修一門基督教 “道義”的課程 。 雖然基督教的傳授是該校的特色,但無形中,我們間接地 從這門教義中 對西洋文化有了 大畧粗淺 刻的認識。基督教支配西歐文化盛衰 並和科學藝術潮流的去從關係密切。尤其是西洋 古典 (Classic )畫中十之八九都與宗教有關,對我以後學習西洋畫作很有幫助,我們住宿的學生,受益更多,我 12 歲時 獨自離開父母和其他不同地方不同年的學生一起生活,養成自律自立的 獨立精神意志,一生享用不盡。
1951 年我回民雄,就讀嘉義中學高中部,以火車通學,又回住父親的畫室。我在課餘開始閱讀畫室內的書籍,當時中小學校都沒有學生用的圖書館,父親的藏書成了我的 Library ,在求知慾旺盛的年歲,這些書籍滿足了不少我的好奇心,也大大地增廣了我不少見識。在美術方 , 日本文新美術講座系列中就有石川欽一郎所著“西洋繪畫史”,石井 柏亭 的風景畫 論, 藤島武二的“人物畫論” ,片多德郎的 “油繪の描方” ,“素描 總”等,另外アトリヱ叢書有“構圖の新研究”等等。我的基本美術知識大部分是閱讀這些日文書籍得來的。
父親在戰後從上海回台灣 後,在嘉義地區的油畫畫友較有來往的只有陳澄波先生,但自從陳先生在 228 事變被槍殺之後,父親就很少有其它畫家朋友。父輩的台灣油畫家們幾乎都是台北師範或國語學校出身,以後都到日本的美術學校習畫。只有父親是台南師範畢業生,又是不喜歡日本而獨自到上海學美術的。
他的思想基本觀念以及長久在大陸滯留的背景,自和他的同輩畫家們大有出入,對一個畫家來說,沒有同行的人能夠一起來談天說地,討論藝術是很寂寞的事,因此當我對美術常識較有基礎的時候,我和他談起藝術的機會也日愈增加,也參與他的一些和藝術有關的活動。他喜歡逛民藝店,參觀雕刻廟神公偶像的雕刻店,為了整理他在大陸收集的中國字畫,我幫他編目錄,著他跑了好幾次嘉義市內裱畫坊,我上大學在台北時還和他去拜訪蒲添生先生,並參觀他的雕塑品。蒲先生是陳澄波先生的女婿,當時他正在塑製鄭成功像,他給我們解說雕塑經過以及鑄銅像的細節。當嘉義縣長林金先生委託父親設計嘉義縣第一屆縣運動大會會旗時,我也參加他的工作,當他的 Draftsman ( 圖案工 ) 設計會旗,當我看到會旗在運動會開幕典禮時被升上,飄揚在嘉義中學操場上時,心裡有說不出的興奮與成就感。
父親的興趣是多方的,除了美術之外,他拉胡琴,唱平劇,打油詩自娛。養植動植物也是他的嗜好,家裡 收集了不少蘭花品種及果樹,其中無花果是台灣稀有的外來植物。我家飼養過的動物種類包羅十二牲畜的大半,雞、鴨、豬、狗、貓、兔子、金魚、鳥類。我們還養過一隻小猴子好幾年,最後送給民雄國校。為了釣 魚他也飼養紅蚯蚓。飼養“半天仔”(小雲雀)是父親喜歡的hobby ,從田野的鳥巢把剛孵出來的鳥帶回家,用他自己獨製的飼料飼養一養就是好幾年,餵鳥是件相當麻煩的工作,尤其是餵小鳥的時候。
為了照顧這些動植物我們孩子們都得幫忙,我手腳好動,被他抓公差,當助手的機會也多,從而也學了不少農藝、園藝以及動物生育的種種知識與技能。我對大自然生物科學的興趣也是在這種環境中培養出來的。
3.實驗科學的研習
實實驗驗科科學學的的研研習習 實驗科學的研習我們高中時候的課程,除了國、英、文史地理、物理化學之外亦有美術、音樂 課,但報考大學時的志願不是文法商,就是理農工醫,幾乎沒有有志於藝術的 學生。這當然和當時台灣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有關,但也可以歸咎於台灣 藝術教育的失敗。我們嘉義中學的美術老師是後來在台灣成名的席德進先生。 但是老師在上課時只教我們在紙上畫些鉛筆畫而已,連最起碼的美術的基本常 識,如畫的欣賞、名畫家及他們的畫風等簡單的美術史及美學的基本觀念都沒 提到。如此教育,也難怪一般人對藝術的無知而且缺乏興趣関注。我們學生總 把音樂美術課當做消遣娛樂,可有可無的“課外活動”。老師也只是應付應 付,當然沒有一個學生會被影響而有志於藝術。
1960 年代的台灣貧窮社會,一般人連基本生活都沒把握的時代,根本沒有藝術市場。學了藝術的人,無法以藝術為專業來糊口。以父親為例,他學了美術,又用了那麼多年的時間專門作畫,結果是連一張畫都沒賣出,母親常譏笑父親的 idealists 的想法與不切實際的活動,“通通都無路用”。
在這種環境下,即使我已對美術因為父親的影響而有較清楚的認識,也和其他很多同學一樣,把上大學的志願放在實用科學有關的科系,我自忖,先學一技容易維持生計的專業,等以後有更好的習畫環境時再來畫也不遲,何況先學科技對學繪畫更有幫助。畫人體動物時要有解剖學的常識,畫風景也要有光學、色彩原理的認識。因此學了自然科學,可以加強我們對人物風景的觀察與感受,從而更能發揮作畫時的表達能力。文藝復興時的大畫家 Leonardo da Vinci(達芬奇)作畫時不以眼前看到的形體而滿足,他更進一步去研究物體構造的裡,外,了解構造的機能,因此他的畫不只代表形狀而且也把更重要的功能也表達得淋漓盡緻,畫出來東西也更生動感人。他對自然的探索影響近代自然科學的研究與應用。他是第一個把藝術科學化的 Renaissance men。
1954 年我第三度離開故鄉,離開父親的畫室上了大學,只好暫時拋開對學習油畫的想法,進入自然科學研習之門。
從台灣大學開始一直到美國 Wisconsin 大學,雖然熱衷於自然科學的研習,但一有空閒的時候就非常想念在故鄉,在父親的畫室的那一段歲月。,在這種時刻,內心裡總會燃起繪畫的慾望,在不自覺中拿起筆來塗鴨做些 Sketches 來“止癢”。
4. 來美習畫經過
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只要有心人。1970 年我來美國已有七年,在科學研習方已告一個段落,但對學畫一直沒有死心,一離開學校,我立刻計劃重整旗鼓做研習油畫的打算。我從學習科技的經驗知道,要學一樣東西尤其是技藝,非得全神貫注持之以恆,不惜經年累月,淬礪琢磨不會得道。因此,首要之務是試煉自己對習畫的 意 與毅力。再次就是一定要製造一個經常可以學習作畫的大環境。但說來容易做起來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有心思 的時候,總是沒有時間,有時間的時候,又反而沒有心思作畫。為了起步開始,就掙扎了一段很長的時候。
這時候剛好父親退休,雙親來美滯留一段時間,有他們在旁,好像又回到我少年時在民雄家裡的時候,父親開始提筆作畫,我又當了他的助手,但這一次不是替他移植蘭花、修剪盆栽、調製動物飼料,而是替他準備畫具畫布,驅車到郊外公園寫生。上一次我看到他用油彩作畫,是在中國杭州的時候。回憶當時再看他來美時開始用油彩的情形,心裡有無限的感慨,我在台灣住在他的畫室時竟沒看他畫過油畫。
父親在1920-30年代在台灣上海兩地學油畫,那時候他的最大遺憾是從來沒有機會看過西洋各大畫家的真品。我們藉此機會參觀美國 , 歐洲各地名美術館的收藏,觀賞名家大作,大開眼界。這些活動也給我很大的啟發與鼓勵,大大地增強了我對油畫研習的決心。
4.1 紐約 Art Students League of New York
父親回台之後,我先在就近成人學校(Adult School )熟悉一下美國 Art Class 的環境與教學方法。我自信在 Drawing 方已有基礎,因此注重水彩與油畫的學習。但是 Adult School 到底是為了 Hobby 而設,沒有正規的畫室設備,我雖然上了好幾個學期,除了藝術材料以及一般的 information 之外,對自己的畫作研習進展,收穫非常有限。我決定找一有畫室的地方,拜師學藝,接受更有系統的專業訓練。
在紐約市 57 街 Carnegie Hall 音樂廳斜對,有一個歷史已有一百多年的美術學校,Art Students League of New York 。這 個學校是專門為有志於 Fine Art 的學子們學畫的地方。全校有十幾間 習作畫室(Studio) ,從油畫水彩到雕塑,Classic 到modern art,用live model 給學生練習創作,自由選擇自由發揮,表達他們的藝術天分。該校宗旨認為 Fine Art 的訓練不在講授而在實際修練,學生全部把時間花在畫室,老師只在旁批評指點開導,因此不修學分也不授學位。學校自創立以來出了不少名家,如 Jackson Pollack 、Georgia Okeefe 、Roy Lichtenstein等。這種訓練學生的方式──導師學徒制──和大學研究生的訓練一樣,強調學生的自發與創作力。
1981 年,我開始到 Art Students League 註冊,再次進入熟悉的 Atelier。
我先在 Daniel Dickerson 的畫室學油畫的基本,半年後轉到 Harvey Dinnerstein的畫室。Dinnerstein 注重學院式(Academic )的訓練,對學生的基本要求甚苛,不收對 Drawing 沒有基礎的初學者。因此班內年青有天分的學生較多,提高了我在他畫室學習興趣。他在畫室和學生一起看模特兒作畫,以身示範。作畫時強調扼要簡化的原則。我在他的畫室兩年,大大地增進了研習油畫的信心。此後,為再吸收更多的油畫技法,我加入 Hillary Holms 的畫室研習 Portrait Painting 一年。
1984 年我申請 Art Student League 會員資格,經 Dinnerstein 的推薦正式成為會員。會員的好處是可以利用為會員而設的畫室作畫,自我研習。每星期六還供應模特兒為會員利用,我因為自己沒有理想的作畫場所,因此盡量利用會員畫室,自加入會員之後直到今天,很少在星期六沒有去 Studio 的時候。
星期六的會員畫室是每週一次畫家們相聚作畫,交換意見心得,互相觀摩批評畫作的地方。我在那裡研習效果不亞於有老師的畫室。會員之中,也有當繪畫老師的,也有各種專業的畫家。聽取他們的批評與比較他們的作品,可以衡量自己進步的程度水平,30 幾年來上這個畫室已成了我生活的例行公事。
4-2 Arthur Maynard 的畫室
我在 Art Students League 習畫時,有人告訴我在 New Jersey 有位老畫家是位很好的老師 Arthur Maynard 。他 在 1960 年代 在 Art Students League 任教,30 年前在 Ridgewood, New Jersey 自設 繪畫研究所 (Ridgewood art Institute) 收徒授藝,培養不少畫家。因為 Ridgewood 離我自宅不遠,我決定去找他習畫,我白天在藥廠研究室工作,星期六又消耗在 Art Students League 的畫室,所以求他能否在週日晚上到他的畫室學習。他說晚上模特兒不好雇,只有一個學生時負擔大 , 也不便。不過他看了我的一些畫作之後大概認為我到底是個很 Serious 的學生,乃答應每週兩夜到他畫室報到。原來他的 Art Institute 內有兩位繪畫教員也有興趣在晚上一起在畫室研究。如此一來大家共同負擔雇用模特兒的費用。有時模特兒欠席,其中一位充當模特兒。我很佩服他們雖然已當老師的人還是那麼敬業繼續研究,不恥下問的精神。
我們作畫時 Maynard 坐在我們背後的沙發一邊閱讀一邊批評我們的進展。他要我們注意整個畫的色調和諧,色譜與明暗的關係。常用西班牙畫家 Velasquez以及美國畫家 John Sergeant 的畫例來討論油畫的構圖用色及筆觸的運用。我在他的畫室 隨他學畫 兩年,直到他去世為止,得了很多啟示。
4-3 Plein air painting ─大自然是我的 Studio
法國印象派畫家們的風景畫,經得起時代的考驗,到今天還是那麼普遍地受歡迎,是因為他們的畫作,不是閉門造車的產物,而是直接在陽光下,把大自然景色中的色彩、光度、空氣在畫布上用油彩表現出來的創作。他們不僅研究光線推移過程對空氣及物體相互的影響,也極重視光線與色彩間互動互補的關係,因此畫出來的作品更能代表我們對自然美的感受,也給人有置身其中的真實感。我們看了這些大家之作,常驚嘆即使平凡簡單的景物,在他們的畫筆下竟會是如此美麗感人!
我沒有真正在陽光下研究油畫之前,對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 )的畫一知半解,以為到外寫生就是外光畫,其實大部分的 Outdoor Sketch 只不過是到外把眼前看到的物體形像畫出為前題,這和 Plein air Painting 的觀念有很大的出入,無論春夏秋冬,在太陽光線的影響支配下的自然物體,色彩與空氣中的水分是那麼複雜多變,在這種自然環境下作畫,實在比在人為控制的畫室作畫困難的多,對我來說,要在野外把所見景色感受表達在畫布上,是個很大的挑戰,好在我小時候在鄉下長大,來美之後,又常在外邊山林露營活動,對大自然的種種環境並不陌生。因此 Plein air Painting 對我特別有吸引力。
1984 年春,我在 Hilary Holms 的畫室時,有一天他的畫友 Curtis Hanson 來代課。Hanson 專業於風景畫,是個道地的 Plain Air Painter。我抓住這個機會走入Plain air painting 之路開始他背著畫架去探究風景畫的世界。果然不到外好好洞察大自然千變萬化的奧妙,要把自然景色的美表現在畫布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Hanson 是 Boston 畫派 William McGregor Paxton 的高徒 R.H. Ives Gammell 畫室訓練出來的畫家,家住風景優美 Connecticut 鄉下,對風景畫特別有深入的研究。自從和他學 Plein air painting 以來,我一有機會就和他一起作畫,我受了他影響與鼓勵,即使在 下雪 的冬天,也不萎縮走出室外寫作,並養成就地完成畫作的習慣,把大自然當作 Atelier 。 在外繪風景的最大困難是 風,雨及 太陽光線的推移而限制可以作畫的時間。有人常問我何苦一定要到外邊作畫,照個像帶回照片來繪畫不是更方便嗎?當然這樣作畫也無可厚非 , 只是我們在外寫作的目的是要把畫家在外邊看到的自然美的感受借景物來表達在畫。
如果不到外親身體會觀察研究,是很難達到我們寫風景畫的目的。這就是畫風景畫的難處。
5. 後記(Epilogue)
我自小受先父劉新祿先生的影響,喜歡工藝美術尤其是繪畫,早年在故鄉的時候,有畫家的父親在傍,又有設備完善的畫室環境,是個學習繪畫良好的機會,可惜沒有把握機會好好利用,坐失良機,直到來了美國之後才再開始認真習畫。其間,起步時的掙扎遇到挫折時的灰心洩氣更不在話下。好在童年時候的憧憬未瞑,作畫的興趣還與年俱增,得能堅持至今。
任何藝術工作首要之務是技巧的把握。以繪畫的觀點來說,如何運用作畫的技能,以線條、筆形狀色彩、筆觸,有韻律、和諧地組合在畫來表達畫家對物象感受的美就是繪畫的藝術 (fine art of painting) ,作畫的技巧與表達能力除了天份之外,只有從不斷的修練、探討得來。有了熟練的技巧與運用的能力才能隨心所欲盡情表達。因此藝術之路是沒有捷徑的,唯有腳踏實地,走一步算一步,隨時以一份耕耘一分收穫來自勉。
藝術之道是永無止境的,藝術家也沒有退休的時候。
此次承蒙太平洋時報李淑櫻女士的支持與鼓勵,才鼓起勇氣把自己很平凡的習畫經歷 記述下來,在此特別表示誠摯的謝意。
Chao-Min Liu
Life member, Art Students League of New York
原文登於太平洋時報 [白鷺鷥欄] 1997 年 11 月 27 日, 2013 年 10 月修訂。
Attached are two recent paintings, all 24 x 20 “ oil on canv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