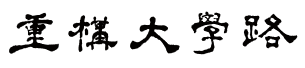天光雲影說烈風

野原跌宕,山水鋪張,牛稠溪水底羅列星斗,浩淼雲天間荒草齊腰,野鹿出沒,陽光雨水年年,綠水無盡。
2020「民雄印象」在地書寫徵文比賽首獎得獎作品
作者/廖鋒燕
繁花盛開的三月,牆頭蝶飛,小雨輕風舞落花。淡紫色的小花搖曳,吹動生命的燦然。昔打貓社舊址福權村,綠色的行道樹,濃蔭匝地,月光如水的夜裡,苦楝花木盈盈的光暈折射打貓豐盈而艱澀的生命輪迴,若苦楝花開花落,一種無法全然透析的生命多樣性,清風拂、花瓣落,蔌蔌清香細…。
蔓草堙路夏日雨滴滴落熱帶的憂鬱,北回歸線之北,莽莽蒼蒼大地,洪雅族Dovoha,意譯「烈風」。17世紀曾經威猛若烈風的打貓部落,月光吞吐千年,水氣氤醞白雲繾綣打貓社,晴雨未定的七月仲夏,我在天光雲影間感悟歷史,在史書攤陳的隻字片語間追思三百年前的洪雅族打貓部落。
我曾有緣在黃昏的晚霞裡遠眺牛稠溪,頂著秋風與微雨走訪打貓街,還在一個個夏夜裡,細數星斗、對話打貓歷史過往,我來此尋景更來尋史,欲在心頭搭建歷史中的打貓,尋覓誠懇天真的洪雅族人臉龐,與其曾經走過的腳跡,在孤黯的角落裡、在遠年的荒堆間搜尋過往的三百年。無奈的是歲月若迷宮,混沌瀰漫於打貓,逝去的人事如離弦的箭簇,無以迴旋,難覓痕跡,打貓社遺留的唯文人筆下半行墨跡,令後世的我匆匆撫摸。
野原跌宕,山水鋪張,牛稠溪水底羅列星斗,浩淼雲天間荒草齊腰,野鹿出沒,陽光雨水年年,綠水無盡。茫茫長草掩映,打貓村社點點,風在干欄式居屋的茅草頂上遛達,竹林繞流水的初民天地裡,四季纍纍然來,無乾坤無日月。過往故事隨光影飄動,煙雲數百年。東榮村、中樂村、西安村一帶舊日打貓社洪雅族活動社域,今青埔地區仍遺留番婆村地名,昔日民雄情事在牛稠溪綠色水藻伸展間,靜靜浮游。天風吹拂民雄數個世紀,這兒曾有17世紀洪雅族的腳跡,社民亦曾豎耳傾聽歲月裙帶撫過野原的窸窣,野草萋迷的漫漫曠野,打貓社民奔走其間,沉睡在柔軟暖風裡,生活是一片閒適安然、與世無爭,日日月月。
歷史搖曳青嶂,1696年4月8日星空伴隨花樹曳影,郁永河「夜渡急水溪、八掌溪,抵達諸羅山;又渡過牛跳溪,經過打貓社。」潮濕的台灣西海岸疆土,一齣傳奇的歷史被書寫,在《裨海記遊》。黃叔璥《打貓社番童夜遊歌》:「麻呵那乃留唎化呢(我想汝愛汝)!麻什緊吁化(我實心待汝)!化散務那乃麻(汝如何愛我)?麻廈劉因那思呂流麻(我今回家,可將何物贈我)!」愛戀濃稠如雙福山琥珀色的黃昏夕陽,一種異文化的碰撞,在17世紀末交織的時空中對話文明的分寸,漢番會晤如詩的雨霧,在海洋西南天地中展開。
文人筆下的番女:「民紋身者,有少婦裸體對客而意色泰然。」洪雅族少女的輕笑美如潮水,流漾海洋般青春的碧藍,漫飛的衣裙若西安村邊翻飛的雲。打貓社沉浸在桃李盛開的春風中,張揚的至情盎然如酒。「翠竹陰陰散犬羊,蠻兒結屋小如箱。年來不用愁兵馬,海外青山盡大唐。」不冠不履,裸以出入,此無懷、葛天之民使打貓村社裡充滿蓊鬱的熱帶想像,浪蕩在竹枝詞的春秋呼吸裡。
清初乾隆年間《嘉義管內採訪冊》描摹打貓社氣象:「有生番歸順潘姓,在打貓街西門外為社,約有一百餘戶。番俗與民居不同,每年二月二十日,通社番男女飲酒作樂,連飲咻叫三天,至十五日,全社番男女起步奔走日有走社。婚姻大事,將社內未娶番男若干人,候齊奔走至番仔橋頭為限,以未嫁番女若干人,依次論配。」原始的文化放達,任生活情事單純浪蕩,無揖讓跪拜禮,無曆日文字,當道德儒教的堆疊擠走原始粗曠,何時有人可以將你的天真質樸刻畫得激動人心?漢番和睦共處的歷史鏡頭仍停格在18世紀中葉乾隆年間,諸羅知縣周芬斗撰寫的〈打貓社詩〉:「慕義馴良首打貓,我來三歲息喧囂,肩輿絕跡官音闇,踏月清歌度洞簫」,深刻描摹漢化的現實,奈何百年之後打貓社文化,竟脆弱得無法延續。當鹿場成為田園,傳統成為難以安居的現實,或漢化或選擇離去,成為無以回頭的命運。
1813年春分,打貓社尪姨以鹿骨占卜,熊熊烈火諭示災難將至的宣告,失去的社域,失去的文化令阿立祖震怒,祖靈哭嚎。多年過去了,人景俱幻,一切彌彌頓頓,沒有人等你,甚至已忘了你從何而來,舊社域殘存的記憶孤獨地徘徊,聽見苦楝花飛落水面哀傷的聲音。
我的腳跡踩踏在福權村街巷,史實遺留於我腦海的記憶翻騰,為逝去的歷史神色悒悒。這兒曾是打貓社的活動範圍,漢番互動的歷史裡,番仔莊、番仔溝莊、社溝等地名仍鮮活挺立在2020民雄時空,眼前景象予我一種徒呼負負、無可奈何的失落。昔日社址番仔庄,歷史的廢墟盡成天光雲影,只容我以舊地名尋思打貓部落舊族想像。原居打猫街的簡、葉、連、吳、謝、蔡等六姓熟番家族在1906年也漸次遷離打貓,多年後怕是夢裡不知身是誰?民雄國中土地下草木掩蔭的冷僻處,挖出舊日洪雅族墓葬,三百年前的屍骨陳列於大、小甕環繞的甕群間,彷彿要在屍骨上用歷史紋身,身分漫漶不可辨識、無需太多敘述更無需再次命名,今日雨水像古老神話裡的苦澀淚水,在泥地上涔涔落下,交錯沉默的輕嘆。
洪雅族命運裸裎,輾轉告別文化、告別民雄,僅將思念留給藍天。歲月青色的火燒成一頭悲傷的鹿,社人不知何往,夜風凜洌,月冷凝,打貓社化作一隻文化中的老蜘蛛,徒留殘絲,風中唏噓。阿立祖崇拜宣告斷絕、語言消失,神祕思想與祖靈崇拜,遺忘,唯留牛稠溪口的風呼嘯。舊社址邊綠色的苦楝樹淡紫色小花繽紛落英猶似當年,若一季鬱鬱的洪雅族文化葬禮,時空留下寧靜給民雄,打貓社族,遠去了…。
打貓歲月細細長,民雄這塊土地深沉若海洋,潮起潮落間,移民來來往往,烈風澎湃。海峽風霧飄蕩著離散的氣味,唐山過台灣,隔海召喚靈魂的鄉愁,先民翻閱生死簿,一頁一頁。披荊斬棘拓墾的故事,在民雄命運多舛的土地上,延伸疆界。遷徙的人注定留駐遠方,當他鄉變故鄉,漢移民在民雄落地生根,承載原鄉文化的異鄉土地上,人文意蘊與歷史風景繚繞若煙霧,拌和在吾民的話語與呼吸間。
17世紀國際競爭的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駐紮過此地,鄭氏王朝經營過,再由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到現代台灣,不同時代的民雄映現不同的風情。漳、泉移民流浪生死的記憶,交織的過往,彷如歲月年輪,一圈又一圈,圈圈都有其跋山涉水的坎坷,血汗交織堅忍心志如烈風,滋養茁壯了民雄。遠年開發史裡,先民扁擔橫挑,日月行於雙福山,山勢起伏的稜線似命運皺摺,忽高忽低。胼手胝足在此延伸閩南文化,原鄉信仰保生大帝、開漳聖王的火種未熄,絮絮戚戚生活情事間,吾民展開屬於民雄的社會人文畫卷。
民雄人祖先跨海而來的故事,血汗滴落生命的根部,日光如血刃,伴隨烈風,一段段無可奈何的失落,橫塗縱抹一頁頁先民開發史。我在史實間尋找歷史的回聲,康熙56年《諸羅縣志》上「諸羅十七莊」的打貓街,刺竹圍成的柵城,漢人駐足拓墾。曾經遍地濕溽煙瘴的打貓,匯聚了漢人偷渡客,早期先民生活潦落、隻瓦無存的飄泊,斬荊開曠的歲月裡,風雨深刻的刮痕在生命裡一道一道。
民雄開台祖的故事,在烈風中漫漫浸潤、細細延伸,以心映心,一張張重重疊疊的臉,一幕幕蕩氣迴腸的悲喜,隨著歲月傷逝在風中,人室俱遠。族裔遷徙的故事,家家不同,但是對於血緣的執著,戶戶皆是。家族譜牒上的名字溯源一個個早期拓墾史跡,民雄文化逐漸匯成張力,蔚為方圓,土地上一脈脈血緣怡然融和。豐收村陳氏開台祖陳青山,康熙六十年來台;菁埔村的何氏、福權村的賴姓皆來自漳州;牛稠莊的張姓與熊姓則是屬於粵省移民;田中央的郭姓來自潮州府饒平…。
橫渡黑水溝,苦惱如亂絲,千里海途蠕動著媽祖信仰,玄遠疎闊的故事裡生命起滅,信仰的波濤一路喧囂,一路由湄州流向民雄。天際閒雲高鳥迴,地上參差的廟宇一座座,慶誠宮媽祖坐立高處,眼底涔涔漾著之於眾生的悲憫,在無盡的冥思裡,持天上聖母經咒,柔軟懷社稷,令生命滄海無遺珠。范謝將軍與順風耳,不變的身姿與面容,注解善惡,破譯人性本色。宮內的交趾陶精品,每一塊雕紋與曲線盪著婆娑的神氣和力度,在光陰遞嬗的靜默深處湛然微笑,一種儆醒和思索的力量,自覺自照方能自得,以修行步向涅槃。
反芻民雄先民嵌過的歷史面貌,雨露風霜裡共寫開發史,「紅柿若出頭,羅漢腳目屎流」,先民心房漲潮的思鄉情緒,若中秋盛開的檳榔花鬚,膨脹再膨脹。此生無望只能寄情縹緲,早期族群械鬥或合作,匯聚了文化的多元性。漳州、泉州、客家先民滴不盡的拚搏血淚,昔日漳、泉械鬥滿地廝殺,歷史染血,仇恨的烏雲搖動起伏雙福山。18世紀的夏季雨水淅瀝在民雄先民無夢的沉睡中,舐風蘸雨械鬥的年代裡往往伴隨瘟疫的悲苦,充滿悲愴的音符,拓墾的磨難伴隨械鬥的癡頑與廝殺的愚昧,無以問天無以索地。冷雨幽窗間,先民吞嚥沉鬱的苦澀,僅能以信仰鏈成救贖的纜索,在轟鳴如雷的雨季中向鬼靈祭奠。鄉野間神仙鬼怪的傳說,庶民文化裡鬼月祭典盛事非大士爺廟莫屬,遠年的抽象記憶遙遠卻撼動人心,傳說逶逶迤迤走進鄉誌、走入大士爺廟裡的碑文:「乾隆間,北港泉州人與打貓漳州人,買賣起釁,…事後,乃以普渡方式舉行祭典,超渡因械鬥死傷之亡魂。」,更有一段段傳奇式的附會故事:「每逢農曆七月打貓頂街每日即陰風慘淡、鬼聲啼哭,民眾驚懼不已。時有…大士顯身,陰風與鬼聲遂皆止息」。大士爺境界唯證乃知,時而晴空飆風雷,大氣隱隱若有物,大士爺赫然在焉,軟身木雕神像,雙眼深觸洞徹陰陽,萬象諸法因緣或生或滅,投射觀音大士救贖生命的期許。鐘鼓鈸盤,重一聲,輕一聲,伴和著耆老靈活流轉的掌故敘事,使宗教多了幾分世俗氣息。三界之內眾生受苦處,文隆橋下放水燈,邀請水中孤魂聆誦聽經,一種超度儀式裡的仁慈與透明,流瀉出屬於民雄人獨特的精神世界。
紅土藍天鳳梨花瀰漫滿眼,現世塵埃間有陽光的香味,夏季季風裡苦楝樹繁葉深垂,青鳥鳴樹顛,若生命的循環顯而復隱、終而復始。我一次次巡行打貓前世今生,藉由歷史或藉由心靈想像親炙吾土、感懷吾民。昨日事隨行雲流水去,社溝保安宮仍鍾磬聲聲,迴盪在民雄晨昏。時間若神龍,穿過凡人脆弱的肉身,民雄前生離亂,此生安穩,由17世紀步向21世紀,走出深黑的泥淵,張望今日吾土氣度遼闊,沈潛之後終歸現世的寧靜。曾經沸騰的血淚令民雄茁壯而老成,用鄉土鏈結探索出屬於民雄族裔的天光雲影,儒釋道哲思蘊之於心,並與民雄寺廟建築互為依存、互為映襯,一幀幀吾民虔誠膜拜的形貌與儀式伴隨香煙繚繞,在文化濡養間,感念生命的豐腴與美好。21世紀大士爺七月普渡依然在進行,鄉民帶著信仰的旗幟朝聖,人群沸沸揚揚香煙如霧,所有的信仰匯聚成遊客,喧嘩連天。當幽秘的宗教玄學更貼近親和蒼生,民雄人以安順樸直的生活貫穿持攝成一部現世金剛經,朝夕禮讚誦讀。歷史迴廊裡吾民一路走來,總在歲月漂洗間,點燃生命眼眉,且讓書香酒香伴烈風,盛滿民雄街肆,在生之歌的起承轉合處,咀嚼迷醉,自有滋味。
天光雲影間烈風春色如許,夏日朝陽依舊染黃了牛稠溪,中秋溪畔仍灑滿朗朗月光,臘盡春回後,門前桃李都飛盡,又見烈風落楝花…。
作者簡介
30年歷史教職生涯, 20載行旅世界,十多年來提筆自娛,書寫半生簡簡單單情事。近年藉歷史探索,欲在鄉土留白處書寫,以達自我生命深邃的呼吸。
複審老師評語
- 李豐楙:專以民雄為主的則特選此篇,題目「烈風」既史亦景,乃指洪雅族Dovoha的意譯。 原本可能是掉書袋的歷史引述,作者借由文學筆調加以淡化,形成民雄的一頁史詩,其中雜錯諸多地名,帶出古今的歷史滄桑:打貓街熟番六姓家族的顯隱變化,象徵洪雅族生活在此的浮沈;從而進入民雄人的世界,借由聚落之號、庄廟之名,象徵漢人社會在斯土的開發札根,其文化象徵即聚焦於媽祖、觀音大士爺,並在信仰遺跡中點綴地名、溪名,交代一篇簡要的村史,文章不長不短,起承轉合猶有餘韻。
- 楊富閔:天光雲影說烈風的「說」字耐人尋味。說字是全文焦點,也是敘事策略,作者對於文史的掌握與詮釋相當自然,加上作者抒情的敘事口吻,娓娓道來關乎地方的一頁發展。
- 楊玉君:作者行文雕琢精緻,縱橫出入打猫數百年之歷史,融鑄移民奮鬥史實於富含感情的筆鋒,自然流露,具有高超的駕馭文字功力。